谁说我妈妈“傻”?她是最完美的母亲
心中有正义良善的规则,犹如灵魂有了信仰,人的生活才会享受更明媚的阳光。 ———作者

徐文弟母亲70岁时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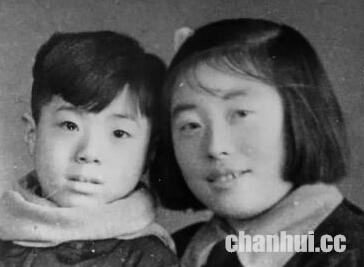
1952年,徐文弟11岁时与弟弟的照片,弟弟被母亲打扮得可招人希罕了
自《新文化报》开辟“扪心”栏目以来,每期我都全部阅读了,特别是今年5月27日刊登的《我因少不更事,深深地刺痛了妈妈的心》一文,使我感触颇深。我也曾因各种不懂事深深地刺痛过我妈妈的心。妈妈是位雷锋式的伟大妈妈,她对我恩重如山,给了我无尽的爱。她就像一粒小小的火星,在我的生命之火即将媳灭时,助我燃起一场熊熊的大火,我的生命因她而精彩。
一
我叫徐文弟,今年76岁,1961年毕业于吉林省邮电学校师资班,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学校因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下马了,我回到家乡汪清县邮电局工作。婚后随丈夫到白城市定居,1997年在白城邮电局退休。
我如今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而我曾经是个被人遗弃的孩子,我的一切都是妈妈给予的。
妈妈一生没有生育,却拥有二女一子,这三个子女都是领养的。我的大姐徐文亚是朝鲜族,我的弟弟朱建华也是朝鲜族。说到这里,读者会问:你们姐弟三人为什么是两个姓氏呢?此事后文再解释吧。我姐姐是6个月时被领养的,怎么领养的我不清楚,但我弟弟朱建华领养时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时我已经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
那是我们家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家属住宅区期间发生的事。有一个从外屯流浪来的两三岁小男孩,天天到各家讨饭,逢人就说:“欧妈,拜比足,拜比足(妈妈,给点饭吃,给点饭吃)……”一个下雨天,妈妈在买菜回家的途中,看到前面人行道上有一群人在围观着什么。妈妈走近一看,是讨饭的那个小男孩倒在地上。只见他佝偻着微微有些颤抖的身子,脏兮兮、黑漆漆的脸颊却泛着红色,双眼紧闭,嘴里吐着白沫。人们只是不断地议论着,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
妈妈仔细一看,这不正是几天前在门前讨饭的小男孩吗?妈妈立刻来到小男孩身边,伸手摸摸小男孩的额头,发现孩子发烧了。她老人家将小男孩抱起来,什么也没说就往家里跑。到了家里给他吃退烧药,又用白酒给他擦前胸、后背、胳膊、手心。妈妈为小男孩忙碌了很长时间,直到病情缓解,又让我煮小米粥喂他吃。
这番照料令小男孩逐渐有了精神,睁开了满怀期盼、可怜的眼睛。小男孩不懂汉语,妈妈就用半生不熟的朝鲜语同他交流。过了三四天,小男孩的病情痊愈了。这孩子也是很可爱的,长得眉清目秀,就是智力有点差。他没有地方去,又不愿意走,妈妈觉得如果不把他收下,他会死掉的……
妈妈决定收养小男孩的事,邻居们得知后都纷纷劝阻妈妈。汉族邻居说:“您都50多岁了,这孩子智力不足,又是朝鲜族孩子,您就不要收养了。”朝鲜族邻居也说:“朱妈妈,听说这孩子的父亲是因脑子有病去世的,这孩子脑子也有毛病,您就不要收养了。”妈妈却耐心地对关心她的邻居们说:“大家平时对小猫小狗都很在意,虽然这个孩子智力较差,但他是一个人啊,我不图他将来对我怎么样,就是要救他一条命。”妈妈深情的话感动了邻居们,他们改变了意见。就这样,小男孩被妈妈收留下来成了我的弟弟。我为弟弟起了一个学名———朱建华。这是1953年5月发生的事。
我弟弟的智力和同龄孩子相比,差距是较大的,比如小学一年级他念了三年才上二年级……
我又是怎么被收养的呢?我是汉族人,家住延吉县朝阳川镇龙浦村,4岁时父亲死了,母亲改嫁没带我。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我成了流浪儿,舅舅家待两天,姑姑家待两天。当时妈妈是那个村的妇女主任,有人看我无家可归实在可怜,就和她商量:“你姑娘已经结婚了,再要个孩子吧!”
我的第一个养父姓徐,所以我和姐姐姓徐,我们姐弟三人不是一个姓。妈妈为我和姐姐没少忍受徐姓养父的打骂。徐姓养父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不喜欢女孩子,因为我姐姐是朝鲜族人的孩子就更加厌恶了,在姐姐刚满16岁时,就将她嫁了出去。
我到这个家后他不允许我跟他们在一桌吃饭,让我在锅台上吃,我妈妈看不下去,他们总因为我吵架。记得一次我不小心将盛满饭的碗掉在地上,养父借机打我。在养父抬起手时,妈妈手疾眼快把我拉进她的怀里,像母鸡护小鸡一样把我全身遮住了。气急败坏的养父看打不到我,就将气全部撒在妈妈身上。他开始时是用手打妈妈,感到不解气就用皮带抽妈妈。妈妈的脊背和头部都受伤了,但她依旧执着地把我护在怀里。妈妈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却不顾自己的疼痛,看我的身体没被打着才放心。从那以后,养父打我便成了家常便饭,但妈妈总是第一时间出现,把我护在怀里或者将我放跑,自己承受着打骂。我上小学时交学费,养父不给,妈妈偷着自己存了点钱,藏在了棚顶上。她踩着炕沿去够钱,没踩稳,一个趔趄摔到地上昏了过去,半天才起来。我那时不知怎么办好,就知道哇哇哭。
后来,我的徐姓养父患了精神病,我的处境更加悲惨了,这种悲惨的日子直到1950年养父病故才结束。现在客观地分析,养父对我们不好,那时他可能就潜伏着轻微的精神障碍,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不然他不会对我们那样残酷无情。
徐姓养父去世后,只剩下我们母女二人生活了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妈妈带我再婚朱姓养父。妈妈再婚的条件是必须带着我,而且我不能改姓,这是唯一的条件,否则免谈婚事,为此妈妈几乎葬送了再婚的幸福。一开始,朱姓养父同意带我,但对于不改姓有些异议,彼时妈妈与他僵持了半年之久才统一认识———我继续姓徐。
关于妈妈再婚时提出的必须带我和我继续姓徐这个条件,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一是妈妈当初收养我时,我的生母因为再婚男方不同意带我,狠心地将我抛弃了,妈妈不想让我再次失去母爱,成为流浪儿;二是妈妈认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为人处世光明磊落的象征,姓氏不能改来改去。我是个9岁的小姑娘,当初被收养时已经随徐姓养父改过了姓,再改姓只能是结婚后随夫姓了。
我第二个养父叫朱连会,山东人,为人很厚道,是天桥岭林业局的八级锻工,月工资99元,属于那个年代的高工资了。他之前没成过家,对我们两个孩子视如己出。
妈妈再婚后,我们随养父搬到天桥岭林业局,我的生活可谓拨云见日,野蛮生长。妈妈性格温柔,脾气特别好,从来不说我,让我自由成长。我小时候淘得没边,像野小子一样,给我买一双胶鞋,一个月穿不上就坏了。我一个女孩子,什么爬山、爬树、跳大墙,什么都敢干……
在林区,我都上初中了还跟一群孩子上山玩,不按时回家,妈妈特别担心我的安全,因为山上不但蛇非常多,还有黑瞎子,小黑瞎子崽在路上经常能碰到。妈妈总是说:“你别总上山玩了,妈看你不回来连饭都咽不下去。”可我哪里肯听妈妈的话,山上的诱惑太大了。那边的山属长白山系老爷岭山脉,没在林区生活过的人不知道,真是太美太美了!每到“五一”前后上山去采菜、采花……“五月节”前后去采草莓,你就去采吧,漫山遍野啊,我们边吃边玩,无比快乐。那草莓跟现在的味道不太一样,简直是太好吃了。
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又不是同一个民族,却有着深厚的情感。这情之深切,若非妈妈的倾情付出,又何以铸成?妈妈对我们三个孩子都非常疼爱,任何人都看不出我们是被收养的孩子。正因如此,也养成了我的任性和坏脾气。在我们姐弟三人中,姐姐和弟弟都很听妈妈的话,特别是姐姐,非常懂事,从不顶嘴,妈妈让她扫地,她连桌子都给擦了;我则不然,让我干啥我总是强词夺理,很少顺从妈妈的意愿。更有甚者,我还总是跟妈妈对着干,且把“傻”字挂在嘴边,一点也不赞同妈妈为人处世的态度。
二
回想妈妈的一生,从来没为自己活过,似乎都是为别人而活。她生活很简朴,一套衣服穿了很多年,却省下钱资助别人,受到了邻居们的交口称赞。
还记得我们家住在天桥岭时五月节做粽子,妈妈让我把蒸好的粽子送给左右邻居家吃。待我送完后,发现家里仅剩下四五个了,气得我哇哇直哭,跺脚地闹。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家东西不够吃还要送给别人?对于我争吃不懂事,妈妈没有责备我,而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他们都是从城市或农业区来的,对于咱们林区吃的东西还不习惯。咱们做些粽子给他们吃,让他们安心在这里生活、工作,没有后顾之忧,这也算咱们为大家做点好事。”
我们家曾经在汪清林业局金沟岭林场住过四五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从金沟岭林场搬回汪清林业局。我那时在长春读中专,暑假回家一看,我们家可热闹了,满院子都是熬药的人,至少有七八伙儿。原来是沟里的人来了,为了省钱不去医院,都住在我们家里。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家里怎么能这样?我简直受不了,大庭广众之下就耍起了脾气。我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指责妈妈:“家里是开大车店的还是开药店的?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什么难听我说什么,让妈妈下不来台,也让来的人无比尴尬。
经我这一闹腾,他们都收摊走了。因为有人走时还拿了家里的几只饭碗,我又不依不饶地跟妈妈吵闹起来:“家里天天有人来,天天有人走,住在咱们家比在大车店好得多,住大车店还得交食宿费,而住咱们家不但不要钱,您还主动给些东西,连饭碗都让人带走了。咱们不欠他们什么,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我这样质问妈妈,可妈妈没有责备我,反而耐心地向我解释:“他们都是我们家住在山沟时的邻居,坐四个多小时的火车来到城里看病不容易,城里又没有亲戚,咱们不帮助他们,谁帮助他们呢?人们之间是要互相帮助的,等你长大就明白了。”然而,妈妈的话我当时并不理解。
那拨熬药的人刚被我赶跑,两三天后金沟岭林场又来了个邻居杨嫂,她也是来汪清治病的。因为她年纪大了,妈妈留她在我们家吃住近一个月,病愈后才回家。杨嫂治病吃住在我们家期间,妈妈成了杨嫂全职的护理员了,天天陪杨嫂去医院看病,回到家后还为杨嫂做饭熬药,真是关怀备至。我很生气,背着杨嫂指责妈妈:“自己家的活让我去做,你却陪着人家,是不是傻啊?”现在想来,妈妈这是助人为乐啊!当时吃的奇缺,许多人都饿病了,来治病熬药的邻居大多数都得了浮肿病,也有的患了肝炎和妇女病,而我却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对于可怜的他们连一双手的温度和一抹视线的温柔都不肯给予;我甚至还把妈妈的良善说成“傻”,现在想来真是羞愧难当。
妈妈这一生做的好事太多,其中有些事让我忍无可忍,那时真的认为妈妈很傻。
记得那是1951年,我们家邻居朴阿孜妈妮(嫂子)连续生三个孩子,孩子们在两三岁时因病都夭折了。她生的第四个孩子在两岁那年,又遇上了前三个孩子同样的病。四处求医未果,朴家害怕极了。妈妈看见后大胆地帮人想办法,竟用土方法给朴嫂子治病。你说我妈妈多傻,竟敢用土方法给人家孩子治病,给人家治坏了怎么办?我劝妈妈也不听,却说:“这孩子得的是小儿疳积病,我有把握。”那时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即使治得及时也会留下后遗症。妈妈就用毛骨朵花、鸡蛋清、黄土混在一起搅拌,均匀后敷在孩子身上,并将孩子下肢用黄土掩埋上。虽然孩子的病果然好了,也没留下后遗症,但妈妈为别人操心太令我生气,这得冒多大的风险啊?!
还有一件事让我心惊胆战。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个年轻的妇女,有精神病,怀着孕,却无家可归。到了冬天特别冷,我妈妈就把厨房铺点稻草,晚上让她在我们家过夜。她得埋汰成啥样啊!披头散发的,口中还念念有词,可吓人了。可我妈非把她整来,我养父也不反对。我又吓又气,都不敢在家待了,大声跟我妈吼:“你傻啊,整个疯子来家里,晚上失火咋整啊?!”
妈妈是个特别勤劳的人,总能靠自己的劳动让我们生活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我们家住在金沟岭的深山老林时,妈妈每年都在开荒种地,那里的土地没有经过深翻的折腾,都是腐殖土。妈妈是种地能手,大头菜、土豆子什么的都长得硕大无比。那时山沟里的蔬菜绝大多数是小火车(一种专门用来把砍伐后的树木运到汪清县城火车站的车,俗称蚂蚁车)从汪清县城运来的,所以金沟岭的人是吃不到当地新鲜蔬菜的,于是妈妈就把早熟的菜分给左邻右舍的人共同享用,因为这件事我和妈妈没少吵闹。
每当蔬菜成熟,妈妈就让我和弟弟各家送菜。那是1959年暑期,我放假从长春回家,妈妈交给我一个任务:去菜地运菜。
从我们家到菜地有一里多路,我也学会了朝鲜族用脑袋顶菜,一次能顶一百多斤。可气的是顶回来你倒吃啊,可妈妈却挨家挨户地送,常常是我头一天顶回来一麻袋菜,第二天就被妈妈送没了,我还得去运菜。我累了,就向妈妈撒气:“您傻啊,啥都给别人,这啥时候是个头儿啊!你看咱们家都让你过成啥样了,人家工资60多块钱的都比咱们家得过得好!”
连平时对妈妈唯命是从的弟弟也和妈妈生气了,他竟把妈妈种的近半亩毛葱用镐全刨掉了。事后妈妈并没有责怪弟弟,她知道弟弟是因为心疼她太辛苦才这样做的。
妈妈就是这样舍己为人,不求回报。我在读中专二年时寒假回家,将自己一年省吃俭用攒下的10斤全国粮票给了妈妈,可是到了第二天妈妈手中仅剩下3斤了,那7斤粮票给出差外省的邻居李家哥哥了。我知道后非常生气,不满地对妈妈说:“您知道那10斤粮票我是怎么攒的吗?我每月才27.5斤的粮票,我是挨着饥饿的啊!我多次托人把10斤饭票换成吉林省地方粮票,又求人把地方的换成全国粮票,可是您全没当回事,轻易地就把您女儿挨着饿给您攒的粮票如草芥般无代价地给人了,真是太傻了……”当时妈妈没有生气,只是流着泪说:“你李哥去外省参加会议,正愁没处兑换全国粮票,我又不去外面,放手里也是闲着。穷家富路嘛,他出去也是有很多地方需要用到的啊……”
把妈妈助人为乐的行为说成傻是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事,因为我刺痛了妈妈的心。还有一件让我永远内疚的事,使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妈妈。我1969年结婚后随丈夫到白城市定居了,虽然养父和弟弟来过,可妈妈却从没来过,所以也没有吃过我们家的一碗饭、喝过我们家的一口水。但在妈妈病逝前一两年曾有来我们家居住的意愿,只是当时我的工作太忙,女儿又在读高中,觉得不是时候,因此我对妈妈说:“等您外孙女考完大学后,我马上把您接到白城来。”可是我女儿考完大学我也没有马上把妈妈接来,直到妈妈病逝。那是1982年正月十三,妈妈75岁。
对此事我简直是追悔莫及,哪知妈妈会走得那样快啊!妈妈辛苦了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汪清县和那里的深山老林,对于我们吉林省最西部白城地区一马平川的景象是没有见过的啊!
三
真正读懂妈妈是在我当了母亲之后。我在初中毕业时,妈妈希望我进入林业局的工厂做车工,我没有同意,而是坚持到省城长春读中专。其实妈妈并不是不想供我读书,只是她不愿让我离开她。当时妈妈可能想了,如果我去外地读书,毕业后一定不会回到她身边的,那时延边地区个别地方还是比较落后的。妈妈的爱女之切,我在自己的女儿考上大学去石家庄读书时体会更深。
女儿同其父乘火车奔往石家庄市,我在白城火车站同他们分别,我不知怎么从火车站返回家中的。火车站到我们家大约15分钟的步行距离,而我却用了一个半小时才走回家中。到家后坐立不安,什么心思都没有,精神恍惚,总感觉女儿在呼唤我。认为女儿在她的卧室学习呢,走近一看,没有。啊!女儿还在学校读书没放学呢,就急忙到窗前向外张望,看了一阵也没看到女儿的身影。对了,女儿刚放学正在路上往家走呢,我得去接她,就风风火火地向女儿的学校飞奔而去……就这样反复想,折腾了一夜,直到天亮。想女儿想得我都要发疯了,幸亏当时的邻居和工作单位的同事们开导我:“孩子上大学是好事儿,是高兴的事儿,这些年你的这些辛苦不就是为了女儿上大学吗?”女儿读书三年我没有一天不想的,联想起妈妈,我从汪清到长春读书时她的心情和我也是一样的啊,甚至比我挂念女儿的心情更强烈。我常常想,妈妈当初为了我宁可遭受丈夫的打骂,为了我不改姓宁可不再婚……我能做到吗?恐怕难以做到。
妈妈生前虽然没给我们留下物质财富,但留给我们的是更珍贵、更丰富、更有意义的精神财富———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不求回报地去帮助他人。关于这一点,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逐渐理解了妈妈,也认同了妈妈的做法,而且我也越来越像妈妈了。比如我丈夫的一位住在农村的姑母,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需要我们的资助,我们把家中积攒的钱拿出来为其购买了一辆胶轮大车、两匹马和12头羊。为此我们拉了不少饥荒,还了四年都没还完。如果没有妈妈在我年少时的言传身教,我是做不到的。
我的养父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林业工人,我的妈妈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但他们却得到了林业局群众和领导的关怀和爱戴。特别是当时汪清林业局职工朝鲜族人居多,而党政一把手全是朝鲜族人,像妈妈这样普通的汉族老太太受到两个民族人们的尊敬实属罕见,这与妈妈的为人分不开。有两件事足以说明妈妈在大家心目中的位置。一是在我初中毕业不久,养父退休弟弟接班了,由于我们的父母人缘好,弟弟接班后汪清林业局的领导们给予了弟弟特殊关照,没有分配弟弟到深山老林伐木区做伐木工作,而是安排弟弟在城里林业局直属厂做车工,他的师父是他的外甥,即我姐姐的长子。弟弟直接分配到城里在当时是不可以的,当大家知道他是朱妈妈的儿子时,从局领导到一般职工,竟没有一个人持不同意见。二是我妈妈病故后,她的寿材是林业局用林区最好的黄花松制作的(里面的松油含量高,抗腐烂);寿衣也是林业局和邻居们制作的。
心中有正义良善的规则,犹如灵魂有了信仰,人的生活才会享受更明媚的阳光。我妈妈从未讲过她的人生哲学,但是却用行动告诉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我曾把“你傻啊”挂在嘴边说妈妈,我们家的亲属也都这么对我说:“瞧你那傻妈!”连妈妈的妹妹都说:“我那傻姐姐。”现在看来,我妈妈那时在她亲人们眼里就是这么傻,净为别人活着;曾几何时我也这么认为,且绝不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我现在不知有多后悔,又有多愧疚。也许妈妈帮助人的方式并不都是那么科学,但她比我想象的更懂得梦想的意义、生活的真谛。有母如此,夫复何求。她不但不傻,而且还永远是最爱我的完美妈妈。
徐文弟
